微信扫一扫
内容页通栏
聊斋诗词鉴赏:夜 电、同长人、乃甫、刘茂功河洲夜饮,即席限韵
41 夜 电(其一)
青石裂破碧天漏,郁郁浓烟蒸宇宙。
玉女无声迸线条,一夜乾坤亦应瘦。
胸中垒块如云屯,万盏灯光和酒吞。
醉中披发作虎叫,天颜辄开为我笑。
天是用何物做成的?上古先民们自然不及我们明白,于是就编一则美丽的神话。《淮南子·览冥训》云:“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既然天须补,那用以补的材料最好与天同质,譬如棉被破了,用布来补而不能用铁,铁桶漏了用铁来堵而不能用木,否则,是既不浑然美观又不牢固耐用的,——所以我猜想天本来就是石头的,不然是承受不住局部重量的。假使我这第一猜测是异想天开,那我的第二猜测应该算是有根有据了吧:最起码,自从女娲补天之后,人们相信局部的石头逐渐变成了整体的石天——民间有一则童谣:“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这说的就是天空和星星。如果说李贺《李凭箜篌引》中的“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还将思维局限在天之一角,那松龄此诗中的“青石裂破碧天漏”,虽说的是淄博顶上这方天,却也可泛指所有的天。因为一则谁也不知道淄博这方天是否正是女娲补过的天,二则天清气朗的时候,整个天空一碧无垠,我们确也看不出补过的痕迹。这样无瘢无麻的一张脸,偶尔“裂破”而“漏”,只仿佛人脸上热极出汗,凉快过来,汗也就干了,脸也就恢复原状,用不着再请女娲来重施修补了。
那天晚间,松龄或许坐在院子里摇着芭蕉扇纳凉,或许在院外的打谷场上漫步构思某篇《聊斋》故事,或许给几个小学生缠着正在仰望星空唱“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的童谣,突然一道电光石火闪过,天空抖抛下一条狂舞的金蛇,照亮了整个宇宙。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倏忽之间,天地一片混沌,凝古今为一时,聚四方为一地,失去了时间,也失去了空间,只剩一个硕大无朋、烟雾崩腾的巨型蒸笼。
汉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左右顾望,恒与一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设有入不出者,天为之噫嘘;矫出而脱误不接者,天为之笑。”矫,指投壶之箭从壶中跃出而手接之复投。松龄奇思妙想,把闪电之光比作玉女投壶之箭划出的线条,大有现代武侠电影之情致。宇宙为一蒸笼,乾坤就男女同室洗起了桑拿澡,仿佛现代体育中运动员的减体重,在一夜电光当中,汗出够了,身体也累瘦了。
此时的松龄,心中磊块不平,好似天上的乌云堆积到了胸间,那就用酒来浇化它吧。谁知一喝就醉了,天上“星星点灯”的万家灯火到哪里去了?不见了,落到酒杯里和酒吞下去了。胸腹之中有这乌云和灯光垫底,松龄恍惚间变成了景阳冈上的武松兼那只吊睛白额大虫,披头散发、据地咆哮。恰值一道闪电飞过,松龄以为苍天给自己的狂态招惹笑了。晋张华注《神异经》云:“言笑者,天口流火照灼。今天不语而有电光,是天笑也。”煞有介事折腾了一宿,看来也是闪电多而雨点少,仿佛打摆子的病人,出过一阵雾露星也就算了。
42 夜 电(其二)
夜深有鼠大如驴,咤咤霹雳啮破书。
疾风窗户自开掩,若有人兮来荏苒。
鬼母啾啾狐狸啸,摄魄摄魂梦惊魇。
城头隐隐鸣鸱枭,闯然一声闪红绡。
关于夸张,鲁迅先生有极精辟的见解:“‘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变成笑话了。”(《且介亭杂文二集·漫谈“漫画”》)过去读唐诗,见“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曹邺《官仓鼠》),觉着老鼠已经够大了,并且老鼠吃粮,斗用来量粮,二者性质上有相似之处,所以“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今天读到松龄的“夜深有鼠大如驴”,觉着比“广州雪花大如席”还好笑。不因为“鼠”和“驴”形体差距太大,据说曹邺的诗一本作“大如牛”,牛比驴还大,我们并不决得好笑;关键是“驴”之一字似乎不宜入诗,一入诗即显得滑稽,这和驴之品相有关。尽管它勤劳、耐苦,农人“不可一日无此君”,但由于脾气倔、相貌差,加之心思迟钝,因此历来被看作是低俗之物,与高雅之诗牵搭不上联系。宋尤袤《全唐诗话》:“相国郑綮善诗。或曰:‘相国近为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此何以得之?’”这只是富贵者对清贫生活的一种书面向往,如果堂堂一品大员真为寻诗而骑驴,若让《儒林外史》里的杜慎卿碰上,定曰:“‘雅’得这样俗。”所以陆游说:“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道中遇微雨》)也只是一种无奈的自我解嘲。至于李白、杜甫、贾岛等的“骑驴”,虽则颇有雅趣,却总有些漫画味道,让人看了鼻酸。譬如刘姥姥骑驴,我们感觉浑成,若让宝黛骑驴到街上一转,肯定会万人空巷。清顺治帝画状元傅以渐骑驴图,题曰:“状元归去驴如飞”,易时谚“状元归去马如飞”之一字,谐谑调侃之味便氤氲满纸矣!
松龄为何说“鼠大如驴”而不说大如虎呢?“虎”和“书”也是押韵的。我想一,可能是就近取比,故意增加一点幽默感,农村里驴不是寻常可见之物吗?二,松龄醉意朦胧当中,可能刚看到一只硕鼠窜过,就恰巧听到了一声驴鸣,于是就有了这神来之笔。——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其二:“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睡梦之中听到了檐铃声(铁马者,檐铃也),由此而过渡到真正的冰河铁马,在构思上与蒲诗属同一机杼。
松龄这首诗,可以看作是整部《聊斋志异》的提纲:大老鼠几乎要成精,稀哩轰隆吞啮着墙角的破书;狂风吹来,门窗自开自掩,影影绰绰之间,似有人缓缓走来;南朝梁任昉《述异记·鬼母》:“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产天下鬼。一产千鬼,朝产之,暮食之。”鬼母吃罢自己的小鬼啾啾鸣哭,狐狸窜来跳去,在呜呜鸣叫;松龄的魂魄被鬼狐摄去,梦中惊醒心旌犹自摇摇;城头上猫头鹰瘮人的叫声时断时续、忽隐忽现,一道闪电划过,像闪过一匹红色的薄绢……这简直不是人住的世界,除了松龄,任谁也想像不出!
诗名为《夜电》,全诗写闪电之下的所见所感,惝恍迷离,惊心动魄,秋夜读之,倍感阴森可怖。
43 同长人、乃甫、刘茂功河洲夜饮,即席限韵(其一)
康熙十三年(1674),松龄三十五岁,仍设帐于淄川县丰泉乡王氏家中。仲秋八月,松龄同王长人、王乃甫、刘茂功共集王长人斋中。同人雅集,乐且未央。于是举网般河之上,饮醇酒、荐芳草,捕鱼捉蟹,追拟赤壁之游。即席限韵,记兹胜会。松龄乘兴写下两首诗。
秉烛清宵汗漫游,般河冲激小山头。
人渔芳草黄昏夜,客醉寒潭绿水秋。
伯仲文章皆大雅,主宾词赋尽风流。
何人海上垂芳饵,一线虹霓月作钩。
生活与事业,在中国古代文人心中,历来是一对矛盾。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中,既高唱“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又低吟“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长苦夜短,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当然,“策高足”和“秉烛游”表面看来并不矛盾:既事功有成又享受生活之达官显贵,代不乏人;但更多的知识分子,却无缘“要路”而长守“贫贱”。农民生活虽然辛苦,但没有鸿鹄之志,做得过且过的燕雀倒也减少了心灵的煎熬;仕宦生活固然求之不易,但一旦成功即可封妻荫子享之无尽。上不能为官,下不愿下地的穷秀才呢?八股文时代,有人出题曰:“三十而立”,有人破题云:“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而不坐也。”这句破题,用来移赠松龄,是再恰当不过了:既无法坐上公堂的太师椅,又无心坐下陋室的小板凳,立在空当里的心情不是好受的。于是就寻一些人生的空隙,秉烛夜游,来疗治寂寥填充空虚和空白。
汗漫游,漫无边际和目的的世外之游。此时的松龄已不是恭恭敬敬的小学生面前谨饬威严的先生,也不是熙攘世人眼里恂恂如也的儒者。他把心灵放在了星期天,让身体走进了洗澡堂。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了,就像那自由自在的般河之水。(般[pán]河,发源于淄川县城东南二十五里处龙泉镇之渭头河,自淄川城南汇入孝妇河。淄川县城古称般阳,因其在般河之阳[北]。)黄昏夜,是具体时间,也点明空中之色彩;绿水秋,是大的时间范围,也说出地面之景致。长长的绿水和圆圆的黄昏之间,有芳芳的草,是鼻嗅;有寒寒的潭,是身感。人在钓鱼、做鱼,客在喝酒、醉倒。王氏兄弟的文章,雍容华赡,有大雅之风度;主人客人的辞赋,美妙清婉,具风流之气骨。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贤主、嘉宾:真可谓“四美具、二难并”了。
在乐兴正浓的时候,月亮升上来了。《庄子·外物》说,任公子弯一大钩、搓一黑色巨绳,用五十头阉割过的肥牛作钓饵,蹲身会稽、投竿东海,每天早晨都在钓鱼。宋赵令畤《侯鲭录》云:“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云‘海上钓鳌客李白’。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钓线?’白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松龄读书多,一下子想起了这两个著名典故,说谁在海上垂着芳香的鱼饵钓鱼啊?彩虹是他的鱼线,明月是他的鱼钩。其实晚上是没有彩虹的,为了说月亮,顺便带出彩虹让它沾了光。
44 同长人、乃甫、刘茂功河洲夜饮,即席限韵(其二)
在讲到《湖上早饭,得肥字》那首诗时,我曾试探着提到《红楼梦》。现在机缘更巧了,忍无可忍,索性一说为快。《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中,探春提议吟诗起社,适值贾云送宝玉两盆白海棠,于是众人就限韵作《咏白海棠》诗。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韵。”说着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诗来,随手一揭,这首诗竟是一首七言律,递与众人看了,都该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诗,又向一个小丫头道:“你随口说一个字来。”那丫头正倚门立着,便说了个“门”字。迎春笑道:“就是门字韵,‘十三元’了。头一个韵定要是这‘门’字。”说着,又要了韵牌匣子过来,抽出“十三元”一屉,又命那小丫头随手拿四块。那丫头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块来。所有诗都以这四个字为韵脚。
松龄们这次做诗,也是“限韵”,具体操作过程我们不得而知,但悬揣当与宝、探们无大异。探春作一首,宝钗作一首,宝玉作一首,黛玉作一首,四人共作四首。第二天湘云到来,诗思奔涌,一挥而成两首。松龄的朋友们做了几首,我们不清楚,松龄也如湘云一般作成两首。从诗中看来,所限之韵是下平声“十一尤”韵中的“游”、“头”、“秋”、“流”、“钩”五字。第二首云:
举网烟波续盛游,一樽霜露小滩头。
星河摇动鼋鼍窟,芦荻吹残雁鹜秋。
日暮酒人眠绿草,夜深渔火乱清流。
壮心忽发濠梁思,独入沧浪把钓钩。
松龄在诗序中说:“举网河上,拟追赤壁之游。”松龄在《超然台》那首诗中早就表达了对苏轼的倾慕,今天晚上触景生情,自然又想起了大苏的泛舟赤壁和著名的前后《赤壁赋》。《后赤壁赋中》有“今者薄暮,举网得鱼”与“霜露既降,木叶尽脱”及“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之句,故松龄云:“举网烟波续盛游,一樽霜露小滩头。”
鼋,就是鳖。三百三十年前的般河中有鳖,我想不稀奇。鼍,即扬子鳄,也就是《聊斋志异·西湖主》中所说的猪婆龙。般河中真有这个?谁也不信。松龄为何写到它呢?鼋和鼍不但字形相似、笔画繁多,能给人一种“奇而古”的感觉,就其真实形体,也都稀奇古怪,有一种丑中见美的奇趣,所以二字自古连用,仿佛《封神榜》里的哼哈二将,缺一不可。再说,诗讲求的是美而非科学论文的讲求真,就如同“莫须有”对岳飞来说是灾难,而对诗歌来说却不失为美德。为凑足音节,松龄顺手拉“鼍”来一用,可以谅解。“芦荻”一句,是典型的老杜句法,让我们想起“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之八)。从天上写到水底,从水草写到飞雁,此联视野极为开阔。
《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从日暮到夜深,喝酒而人眠芳草,打鱼而火乱清流,看到自由而乐的游鱼,松龄想起了比东坡资格更老的前辈逍遥者庄子,他要独入沧浪之水,去做钓鱼翁了。
内容页尾部广告
-
上一条:10月11日颜奶奶金身开光仪式
-
下一条:《影观》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同城小程序
同城小程序 房产小程序
房产小程序 商城小程序
商城小程序 招聘小程序
招聘小程序 相亲小程序
相亲小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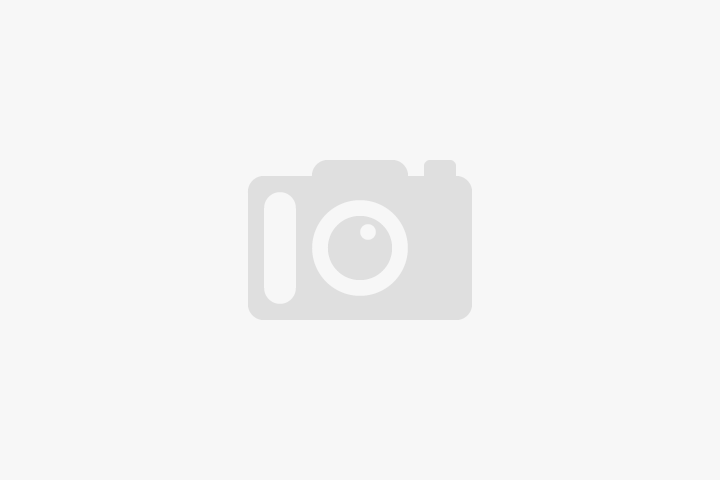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30402000101号
鲁公网安备 370304020001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