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扫一扫
内容页通栏
苏村的冬天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张宗帅
张宗帅,1991年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艺学硕士,山东博山文化研究院研究顾问。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文化变迁,对小城镇与农村的文化制度、小城镇青年与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研究有较大兴趣。多次参加全国各地的农村调研实践,研究农村居住位置变迁的文章《苏村的冬天》发表在上海大学“农村与城市文化研究中心”;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百村调研项目”,在广西都安县、贵州台江县进行农村入户调研,写出了《顺安村的叙事》、《雾迷黔村》等农村考察报告;在新疆伊犁地区进行的采访调研,写成《新疆伊犁地区70-80年代农村干部访谈录》,探讨在70-80年代伊犁农村社会变革及民族地区语言文化交流、社会变迁。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缘 起
写作这篇文章完全不是因为泛滥的乡愁,而是因为意识到我所生长的农村——苏村已经或者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意识到的“变化”,其实也不过是一种感觉化的印象,缺乏实际的调查数据、研究材料的支撑,但是经验主义素描式的叙事,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也往往成为做进一步研究的先导。我越是试图去认真思考苏村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就越是发现我对于自己的苏村的无知。我所遇到是一些别人对我的提问,比如,一个拉送家具的汽车司机问我:“以后村里这些没人住的房子怎么办?现在好些村子里住的都是老弱病残,好多房子、土地眼看着慢慢塌掉、废掉。”他甚至进一步问我:“你觉得下一步的趋势是什么?能再集合起来?”他的意思是汽车行驶过的道路两旁的大大小小的个人工厂以后是越来越多,还是政策改变,像村集体时候那样再把这些个人的企业集中起来。在我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我的看法之后我才发现,汽车司机在提问我之前,他的心中已经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他对我的提问只不过是一种对自己答案的确认。他说:“我觉得再集合起来不大可能,个人的东西一旦放给了个人,再想收回去就太难了。只能走美国的政策,越来越像美国。”我提到这个拉送家具的汽车司机,不是想争论观点的对错,而是说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思考。而我自己则对这些貌似和自己无关的问题没有自己的看法,因为我对于“家”、“村”、“乡”的了解实在少之又少。
我试图思考汽车司机提出的问题:现在好多村子没大有人了,住的都是老弱病残,村里这些老房子怎么办,山区的个人自留地怎么办?他的“怎么办”,是一个意涵丰富的提问句。以我居住的村子——苏村为例,吸引村里人搬到镇上、区里、市里去的主要原因,是所居住的房屋的构造和位置的不同:包括楼房和平房的不同,房屋所处位置的中心和边缘的不同。高层的居民楼意味着体面、干净、舒适的居住条件;位于城镇的居民楼则因为位于“中心”而具有优越的商业、教育、医疗资源条件,这些是搬离农村最基础性的原因。
一
苏村聚居位置的四次迁移
“去住楼”这三个字,首先意味着一种“体面”的、比在村里住平房更“高档”的生活。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房子”,房子本身的构造和房子所在的地理位置成为吸引村里人的最主要的因素。从居民小区楼房本身的结构设计并且从苏村人看待问题的角度出发,相比于村里的平房,楼房主要的优点在于冬天住起来更暖和,对于地处冬季寒冷的北方的苏村来说,冬季取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仅是因为楼房的墙体更厚,从横的方面看,每幢楼与每幢楼之间的前后排列,对冬季的寒风形成遮挡;从纵的方面看,每幢楼内部楼层与楼层之间的叠加,更容易保存热量。正因此,苏村及其附近的村庄产生了季节性的“移居”现象:冬天苏村及附近村庄的人选择去城镇楼房居住,其中有的人是直接在城镇购买属于自己的楼房,而许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则更多选择在具备集体供暖条件的城镇楼房进行季节性的租住。相比于年轻人,老年人冬天更怕冷,对于热量有更高的需求。如果冬天居住在苏村的平房,则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顺着窄窄的台阶下到低于院子平面的“地炉”去“看火”,这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活动,同时也意味着较大的安全风险,比如下雪天“地炉”的台阶比较湿滑,容易摔倒。到了夏天,由于苏村地处山区,夏季气温远低于城里,苏村人又重新回到苏村避暑。这种季节性的移居能够实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冬季处于一段漫长的农闲期,地里没有农活,而且苏村人种植冬小麦的越来越少,即便种植了冬小麦,也不需要在冬季进行田间管理和劳作。
居民楼对苏村人另一个重要的吸引力在于相比于平房更为整洁、卫生,楼房的洗浴、厕所、卫生状态远好于平房,在夏天蚊虫也较少,总体上更为干净和封闭。平房作为一个半开放的空间,和土地、空气有更多的接触面积,更容易接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属于半暴露的的场所,泥土、污垢和灰尘更容易被带进屋内。而楼房作为一个封闭的空间,较少和外部环境发生关系。
从平房本身来说,平房的建造年代比较久远,苏村的平房以老房子居多,老房子就需要经常性地进行维护和装修,如果维护的价格过于昂贵,苏村人自然会选择放弃老房子。但是情况也有例外,以苏村的张家大哥为例,他将苏村“老家”的一进院落以很便宜的价格从几个长辈手中买下来,并花了两万多块钱进行装修,他的“固执”引起了他的妻子的不满,他的妻子认为这里交通不方面,不值得为这些破房子花这么多钱,但是张大哥说:“我就住这里,哪里也不去。”苏村人嘴里说的“老家”就是苏村最早的一片聚居区,位于苏村地势较低的村口处,两边山岭,背靠北面的山,中间凹洼,房屋都是四合院格局,一个四合院往往是一个家族的,每间屋子往往住一个核心家庭。后来因为人口的繁衍,最早的这一低洼处已经不能满足新成长起来的苏村人的用地需求,于是苏村人开始往西边的地势更高的西北边山岭迁移,这是苏村人的第一次迁移,这次迁移到的新聚居地,苏村人广泛的称之为“山上”。“老家”则以爷爷奶奶辈的老人居住为主,出生于50、60年代的父亲辈们则普遍在“山上”建起了自己的新家,实现了和爷爷辈们的分家。而我们这些出生在“山上”儿子辈们,从小就频繁的往返游走于“山上”和“老家”之间,充当父母和爷爷奶奶们的信使。这样的村庄空间布局,也使得我们这些小孩子有了极大的活动和撒欢撒谎的自由空间:比如,我们对父母谎称去了奶奶家,同时对爷爷奶奶说我们回家去了,其实我们凑在一起在村子里四处游荡。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父母们正在如火如荼的挣钱,也正是这些钱使他们实现了苏村聚居地的第二次迁移。在我们这些儿子辈生长的90年代,苏村的主要产业——日用玻璃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日用玻璃的销售市场和经济效益日益快速增长,苏村经济飞速发展,在玻璃工厂上班的苏村人挣的工资越来越多,较高的工资水平吸引了很多外地人来苏村的玻璃工厂工作,甚至有不少外地人选择在苏村定居。快速增长的经济收入使得苏村人对居住条件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伴随这苏村工厂规模的扩张,苏村有了自己的建筑工队,就是这些建造工厂的建筑工队在苏村地势更高的山上开山炸石,修建了真正的楼房和“将军楼”,实现了苏村聚居地的第二次迁移,也就是这第二次迁移,苏村的贫富差距才真正的“视觉化”和“位置化”,从此时开始,住到“楼上”还是不住在“楼上”,成为区分贫富的重要标杆,贫富差距在房子的结构和所处的位置上体现出来,开始明显的空间化了。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苏村90年代修建了现代化的居民楼群——齐城小区,苏村村民相比于周围其它村庄较早地住进了干净的楼房。2015年“旧房改造”项目在苏村最早的村民聚居地进行老式平房的拆迁,改建成新式的高层居民楼。所以在苏村楼房并不是稀缺资源,村里的这些楼房就房屋结构来说,和城里的楼房没有任何不同。但是这些住在楼房小区的村民还是选择去城里购置新房,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房屋位置和交通条件。村里即便有楼房,无奈苏村交通不方便,距离集镇、商业中心太远,生活、购物、小孩上学、老人就医都极为不便。苏村在21世纪以前一直有自己的小学和幼儿园,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效果,苏村适龄儿童减少,以致当年本村学生数目不足以组成一个班,最后苏村小学撤销,苏村的学生开始去镇上、区里上学。为了让年幼的孩子免于城镇和村子之间的长途跋涉之苦,很多苏村人选择在城镇购房。对于苏村的适婚青年来说,拥有一套城里的楼房成为他们婚姻得以实现的必要和前提条件。以苏村的一位男青年为例,该青年在介绍对象的时候,女方明确要求只有男方在城镇买楼,她才会答应嫁给他,男青年的母亲坚决不同意这个条件,最终男女双方没有继续发展下去,直到男方几年之后找不到媳妇,男方父母着急便立刻在城镇买楼,男青年很快找到对象并结婚。所以苏村参加工作了的男青年,他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攒钱在城镇买新房。从女方的角度看待这一现象,“逼迫”自己未来的丈夫在城镇买房,实际上造成了在未结婚之前就实现了男方与男方家庭的分家。一般男方父母因为长期习惯了农村生活而不愿意跟随儿子搬去城镇楼房,从而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婆媳、家庭矛盾。只有在儿媳生孩子期间以及孩子正式上学之前需要照看的时候,男方家长才会去“楼上”跟儿子儿媳短时期住在一起,日后随着孩子长大,住房空间的紧张和男方父母义务感的消失,男方父母倾向于重新回到苏村。这也就解释了苏村聚居地的第三次和第四次迁移是如何发生的。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二
苏村的风水观念
第三次迁移便是从地势更高,其实是已经在山中的齐城小区和将军楼群迁移到苏村以外的城镇中去,以齐城小区居民为主的苏村人开始离开苏村去镇上、区里、市里购买楼房。也就是从这第三次居住地的迁移开始,苏村人口开始外流,苏村迎来了它的“衰落”,“村里没人了”,因此苏村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正是在开山炸石建造齐城小区的时候,破坏了苏村北山的风水,从此苏村才开始“衰落”。风水观念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将会处处体现在苏村人的行为举止和认识情感之中。齐城小区由最初的两栋逐渐发展为四栋,第四栋的位置已经距离苏村最早“起源”的位置只有不到一百米的距离。在这个苏村“起源”的位置,树立着一块石碑,石碑并不是苏村人立的,而是由位于苏村西北几公里之外的福山村苏姓树立的。这块石碑回答了苏村名称的由来,苏村为什么叫苏村?苏村最早的居民是在地势较低的位于今天的铁路位置,但是人口很少,苏村真正成为规模,成为一个村庄,并且被命名为“苏村”,开始于苏千、苏万这两兄弟的到来,他们从别的地方迁移而来,看中了如今福山村人立碑的地方,这个地方位于苏村北山虎头峪的怀抱之中,在苏村人的观念中,苏村背面的北山像一只卧着的老虎,而虎头峪正是老虎的头部和前怀,苏千、苏万兄弟就在虎头峪的山怀里定居下来,因为他们认为此地的风水正像一把太师椅,风水极佳。除了叫虎头峪这个名称以外,立碑的地方还有一个更古老的名称叫“蝎子岭”,用一种现代的解释来看,蝎子岭的命名来源于这个地方适宜于蝎子的生存,据一位看山人说,在这里一天能掀到一矿泉水瓶子的蝎子。但是更古老的传说则说明,蝎子岭的命名来自风水传说,同样跟苏千、苏万这两兄弟有关,传说苏氏兄弟在为自己挑选理想的坟地的时候,请来了“南蛮”的风水师(“南蛮”是北方人对南方人称呼),这个“南蛮”为苏氏兄弟挑选的坟地同样是位于蝎子岭,风水师不仅为他们选定了准确的埋葬位置,还为他们规定了墓穴埋葬的深度,苏氏兄弟在挖掘自己的坟地的时候,按照风水师的叮嘱挖到了规定的深度,此时他们在土里发现了一个宝盒,这使他们确信此地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同时贪欲使他们认为此地如果自己的坟地挖得越深,以后自己的后代便越是能够享受更多的福气,于是苏氏兄弟就超过了风水师规定的深度,继续往深处挖,此时他们突然发现了一道亮光,一只巨大的蝎子从土坑中跑出,苏氏兄弟并没有深究跑出来的蝎子意味着什么。在苏氏兄弟死后,他们埋葬到了自己挖好的坟地中,但是奇怪的是,从此苏氏一家只生女孩不生男孩,这时苏家才意识到,他们因为不按风水师规定的深度而继续往下挖,破坏了风水,他们这一家将要断后,于是苏氏一家决定迁往苏村西北的福山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苏村被命名为苏村,但是苏村竟没有一家人姓苏,相反,苏村西北的福山村则以苏姓为主。让我们还是回到齐城小区,因为齐城小区同样位于这块叫做蝎子岭的风水宝地,修建这些新式楼房的时候,用了大量的炸药在北山的“虎身”上炸出了一片平坦的地基,因此苏村人认为,大规模的炸山同样破坏了苏村北山的风水。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风水破坏只是苏村第三次居住地迁移的后来的一种具有神话色彩的解释,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原因在在于:21世纪以后,苏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居住环境的恶化。首先,以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办企业玻璃工厂,在21世纪以后,已经彻底的私有化,变成了个人所有制。这些从集体村社队企业独立出来的“个人”的厂长,开始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工厂,而苏村因为土地的紧张和交通的不变,必然促使这些苏村能人去苏村之外土地和交通成本更低的其它地方建立自己的工厂,工厂的外迁必然带来苏村经济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随着工厂搬迁到其它地方的苏村人,必然会选择在苏村以外购买住房。而对于仍然留在苏村的工厂来说,则引进了新的生产技术——机械手,从而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样也意味着留下来的劳动者要忍受更低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新成长起来的孩子辈们则不愿意从事像父母那样辛苦的工作,认为在玻璃工厂工作是一种“受罪”,长期从事玻璃生产确实会对身体健康产生较为严重的危害,年轻一代亲眼目睹了自己父母一辈因为从事玻璃生产而带来的健康危害,在他们看来,这种工作实在不值得追求,“玻璃厂的活路不是个好活路”,他们更多选择苏村以外的地方去从事劳动强度较低、工资更高的服务业。这样,去外面寻找合适的工作,也成为苏村人减少的原因。其次,儿子辈们的长大,孙子辈们出生,儿子结婚、孙子上学使得“房子”成为苏村人的“刚需”。对于具备了较强的经济条件的苏村的富裕阶层(主要以成为工厂主的父亲辈们)来说,随着城镇大规模商品房的开发,在外购买商品房成为他们投资理财的一种方式。除了这些外来的拉力之外,苏村人外迁的一个主要推力在于,21世纪以来苏村居住环境的恶化。苏村一直以来都受到缺水的威胁,苏村村里竟然没有一口水井,唯一的一口井还是在农业学大寨时期,在北山后面的山谷里打的,但是因为距离遥远,很少人去那里打水。用水的困难的确使苏村人苦不堪言,虽然苏村很早就用上了从其它地方引来的自然水,但是水质极差,并且是定时供水。随着苏村21世纪以来,苏村癌症患者的增多,苏村人便开始相信苏村的水不行,能够致癌,水质变坏的原因在于苏村工厂的污水直接排放到废井中,地下水受到污染。所有这些原因都造成了苏村人聚居地的第三次迁移。
楼房和平房的区别,是两种生活方式、习惯的不同,而不是思维、观念的不同。即便村里的农民进城住楼,改变的只是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而不是思维、价值和情感观念。以苏村的李姓人家和焦姓人家为例,两户人家都在城镇购买了楼房,但两户人家同时都在楼下阳台外面“开辟”了菜地,甚至在水泥地上铺上厚厚的泥土来进行种植。居住方式的改变,真正改变的是工作谋生方式的改变。以苏村的老岳为例,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是还具有工作的能力和欲望,从他自己对于不去住楼的原因的叙述来看,进城住楼对他来说,意味着他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要通过“花钱”获得,也就是一切都得“买”,而他更喜欢自己种菜,吃自己种的粮食,习惯自己从山上、地里打柴收集燃料,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不花钱,但是住楼无疑就会增加他的生活开支。老岳说:冬天他如果冷了,可以直接去外面地里去捆一捆柴火来,塞到炉子里点着,屋里就暖和了,但是要是进城住楼,则每年都要交一笔价格不菲的取暖费,你不交钱人家说给你停气就给你停气。更为根本的经济上的原因则在于,以老岳为代表的这些苏村的“老头”,他们虽然还具有很强的劳动的能力和意愿,但是他们一旦进城参与到城市“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他们基本上没有竞争力,因而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相比于城市对劳动力的严苛要求,村里的小工厂对劳动者年龄和身体状况的要求则宽松自由得多。而且老岳可以在村里家门口上班,交通成本几乎为零,进厂不离家。而进城打工则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如在村里有归属感和安全感。更重要的一个客观条件在于,苏村存在众多的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他们吸收了苏村本村大部分的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对于小工厂来说,女性(年龄较大的女性)和老人可以支付较低的工资,劳动力成本较低,对于女性和老人来说,小工厂对于年龄、劳动能力等要求较低,并且能够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上班。
以上的例子是想探讨,农村人进城居住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一方面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但是基本的假设可以得出,进城居住楼房,对于大半辈子住惯了平房的农民来说,更为根本的是生活方式,也就是工作和谋生方式的改变,但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为从他们自己的心理认同来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居住到城里就是城里人,而且他们的主要的亲戚关系都在农村,即便自己的亲戚们也住到了城里,他们的交际也是以亲戚血缘关系为单位的,这使得他们对于城市生活没有认同感,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很“贵”,他们的工作虽然相比于农村要轻松不少,工资水平也较高,但是同样他们在城市的花销也相应较高。以苏村南边几十公里之外李村的杜姓男子为例,他今年40多岁,虽然他在市里租住了楼房,并且凭借关系找到了一份很轻松的工作,但是他的盘算是在城里攒够四五万块钱,然后回到李村翻修一下自己在李村的房子,等自己老了的时候还是回到李村养老。老杜以前在李村的职业为采药,采药是季节性的,只能秋后采掘,这导致了老杜收入的不稳定,老杜算了一笔账,平均下来,他每天能挣六十多块钱;现在老杜在城里的工作是道路清洁工,工作很轻松,同事跟他关系也不错,而且老杜平均每天能挣八十多。以前老杜在山里采药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在山里跋涉一天都一无所获,身上的衣服也经常被山上的树枝刮破,被石头磨破,但是老杜自己说,虽然很多时候在山上转一天什么都挖不到,但是那时候还是觉得很高兴,在山里身体舒服心情愉悦,虽然赚钱少,但是觉得自己干的工作很有意义。现在虽然在城里挣得多,但是还是老想回老家。老杜的女儿认为,自己的父亲来到城里居住后,见了世面,每天接触的人也多了,但是老杜身上那些根本性的价值观念没有发生改变。
老杜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苏村聚居地的第四次迁移,也就是从城镇往农村的“回流”。对于出于儿子结婚需要而在外买房的父亲辈们,随着孙子辈们到了上学的年龄,在城里给儿子们“看孩子”的父亲辈们失去了“看孩子”的义务,随着自己年龄渐长而日渐增加的对“家乡”的故土之思,对城市生活的诸多不适,促使他们重新回到自己的“山上”居住。而苏村也发生了改变,比如选择了新的水源地,铺设了新的自来水管道,使得苏村的用水条件改善。同时,苏村道路条件进行了改造升级,家用轿车的普及,也使得苏村的交通条件改善。这些都使得苏村又开始具有了一定的吸引力。比如居住在“山上”胡同里的岳大爷,在今年夏天就重新搬回胡同里,因为自己城里的孙子长大上学不需要自己照料了。岳大爷拂去客厅索尼牌的老式电视机上的灰尘,接上电后发现这台电视机的显影仍然相当清晰,这让岳大爷感慨不已,想到这台日本货还是30年前自己刚搬到“山上”新家时候买的,那时候自己的儿子正好是现在自己的孙子那么大年龄。这台电视还曾经在一个炎热的夏天被岳大爷搬到胡同口,街坊四邻围起来看节目,摇着蒲扇,穿着背心裤衩,啃着西瓜。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岳大爷的儿子们,已然是城市中产,他们将会追随父亲的脚步再一次回到农村,但是他们不是像岳大爷一样回到自己生长的苏村,而是“回到”那些更偏远,环境更为优美的小山村,买下村里的老房子进行装修改造,成为一家三口的乡下度假别墅。这种典型现象体现在苏村西北边几十公里之外的西厢村,西厢村位于山区,更重要的是西厢村环境十分优美,村内溪水潺潺,夏天尤为凉爽,有此地的小桂林之称,宛如世外桃源。相比于西厢村,苏村没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没有丰富的地上河流,这主要归因于苏村地下历史上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而多年的开采使得苏村的地下被挖空,地上水流都渗入到地下。苏村无法像西厢村那样成为旅游村,同时苏村不像北面的平原地区那样有大片平坦的土地,也不像那边山区那样有成片的果园,这使得苏村的土地无法流转起来,进行合作化生产。苏村的土地和住房逐渐在被苏村大大小小的工厂用地所“蚕食”,很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消息,声称苏村以后会整个将村民迁出,将苏村建成一个工业园。但是拆迁的成本显然太高,对于苏村里数目众多的大大小小的工厂来说,占用耕地相对于占用住房用地是一种成本更低的选择,占用了农村耕地的工厂每年向被占用土地使用者支付一定赔偿金。不过,将旧村落整个的拆迁,将村民搬迁进村落旁边新建的楼房,将拆迁出来的土地建设成大型的工业园,这种做法已经在离苏村不远的几个村落开始实行。这种拆迁得以进行的主要动力来自政府决策,迁入该村的工厂原先位于城区西郊,由于紧邻城区,该工厂在成为主要的纳税大户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了减少对城区的污染,政府决定在远离城区的福山村建立一个工业园区。苏村相比于福山村面积要小得多,而且地形崎岖,没有成片的平整土地,所以不会被单个大型的工厂所占用。不过,在苏村的内部空间却正在被整个的“工厂化”,众多的小型的个人工厂,在“老家”“山上”“楼上”全面开花,到处都是小工厂,将原先用于居住的平房改造扩建为小型的工厂,这样的风险更小,成本更低。而苏村的这种小型的工厂所进行的生产,都紧紧围绕着苏村八九十年代以来最主要的工业产品——玻璃。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内容页尾部广告
-
上一条:重修怡园鱼池记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同城小程序
同城小程序 房产小程序
房产小程序 商城小程序
商城小程序 招聘小程序
招聘小程序 相亲小程序
相亲小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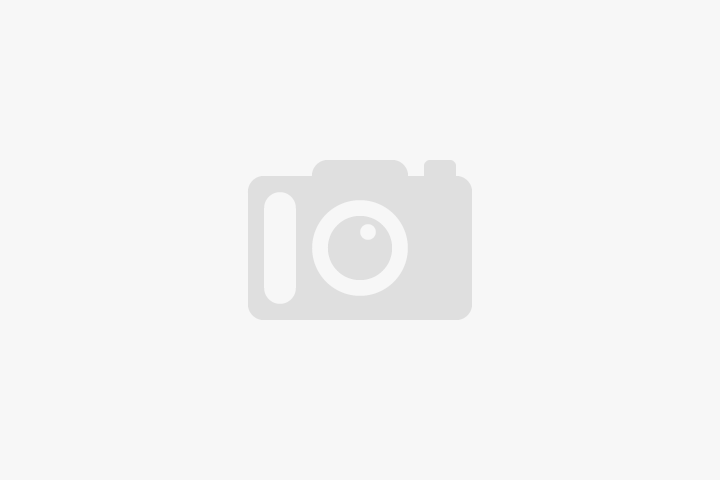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30402000101号
鲁公网安备 37030402000101号